有一次,佛陀來到跋祇國的毘舍離城,住在跋耆族村落附近,一條名叫跋求摩河河邊的薩羅梨林中。
那時,佛陀教導比丘們不淨觀,鼓勵比丘們修不淨觀,說修不淨觀能有大成就、大福利。
教導了這個法門後,佛陀就作了半個月的閉關禪修,除了一位照顧飲食的護關者外,佛陀不希望有任何其他人到他的住處去,而大家也都遵照佛陀的意思,在這期間沒有人去打擾。
比丘們在這段期間,勤修不淨觀,以致許多比丘對自己的身體感到厭惡,結果有拿刀自殺的,有服毒自殺的,有上吊、跳崖自殺的,也有請求其他比丘為自己結束性命的。
有一位厭惡自己身體的比丘,找了一位名叫鹿林的外道,以自己隨身衣物贈送為交換條件,要求鹿林外道殺他。
鹿林外道殺了這位比丘後,到跋求摩河河邊洗刀,邊洗邊想:「我就貪圖這點小利而殺人?」不禁有了悔意。
這時,空中正好有位魔界天眾,知道了鹿林外道的想法,反而鼓勵他說:
「善哉!善哉!大賢人!你這麼做,可以得到無量的功德,因為你幫助了一個持戒有德的釋迦弟子,使他未解脫涅槃而得解脫涅槃,而且,你還可以得到他的隨身衣物呢。」
鹿林外道聽了這樣的讚歎與鼓勵,真以為他這麼做,有大功德可得,於是,他就帶著刀子,到比丘們住的房舍、經行處、禪房等處,主動出擊,見了比 丘就問,哪裡有未得解脫涅槃的持戒有德比丘,需要他服務的。這時,一些厭惡自己身體的比丘,紛紛出來,要求鹿林外道殺他們。結果,半個月內一共死了六十位 比丘。
半個月過去了,佛陀結束他的閉關禪修,出來主持每月十五日的布薩說戒。布薩會中,佛陀發現與會的比丘減少了很多,就詢問尊者阿難。尊者阿難就將事情的原委,向佛陀報告,並請求佛陀再教導不淨觀以外的修法。
於是,佛陀說:
「比丘們!為此,今天我來為大家說安那般那念。這是一個從細微處下手學習,以開展自己的覺察力,而達到止息一切已起、未起的惡不善法,其威力,就像能洗滌一切已起、未起塵埃的大雨。如何修呢?
比丘若住在城郊、村外,早上進入村落乞食時,應好好守護著六根,看住自己的心念。餐後,就到林中、樹下、空地,或安靜的房舍中,端身正坐,將 注意力集中在當前,不去想過去、未來的事,暫時將貪欲、瞋恚、瞌睡、不安、疑問等修學障礙排除,然後學習覺察自己的每一個吸氣與呼氣;覺察每個長、短氣 息;覺察吸氣、呼氣的每一個過程;覺察吸氣、呼氣漸趨細緩的變化;於每個吸氣、呼氣中,覺察踊動之喜、溫馨之樂、覺知感受之心行、心行的止息等感受上不同 的強、淡變化;於每個吸氣、呼氣中,覺察愉悅、止定、解脫等心念的變化;於每個吸氣、呼氣中,觀察無常、斷、無欲、寂滅等現象法的變化,這就叫做修安那般 那念,是一種能讓身、心得到止息,有覺、有觀、寂滅、純一,成就離無明的明分想修學。」
按語:
一、本則故事取材自《雜阿含第八○九經》、《相應部第五四相應第九經》、《雜阿含第八○三經》、《相應部第五四相應第一經》。
二、這個故事,除了成為佛陀教導安那般那念修學法門的因緣外,也是佛陀為出家眾制定「殺戒」的因緣,廣為各部律典所記載。事件的發生地,多數 典籍都略為毘舍離,而《雜阿含第八○九經》作「金剛聚落跋求摩河側薩羅梨林中」。其中,「金剛」即「跋耆」的另譯,而毘舍離一帶的居民,大半是跋耆族人 (參考印順法師《以佛法研究佛法》第六一頁),《雜阿含第九八○經》就稱毘舍離為「跋耆人間」。所以,《雜阿含第八○九經》的記載,只是詳略之別,而實無 不同。
三、依各部律典,幫助別人自殺,或鼓勵、讚歎別人自殺,都等同於親手殺人,而包含在喪失出家資格的殺罪中,但卻不包括自殺。不過,從本則故 事知道,自殺並不為佛陀所鼓勵,否則也不會有安那般那念的教導了。另,《四分律》、《五分律》與《薩婆多部毘尼摩得勒伽》等律典,將自殺未遂者歸於「偷羅 (蘭)遮罪」(大正大藏經二二冊第七、九八三頁,二三冊第六四一頁)。不過,「偷蘭遮罪」一項,是七種犯罪歸類(七犯聚)所特有的。七犯聚的分類,並不屬 於佛陀時代,而是約為西元前二七○年前後,部派開始再分化時代才成立的(參考印順法師《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第二二二頁、《印度佛教思想史》第四五頁)。
四、安那般那,意思是「入、出息」,也就是指我們的呼吸。安那般那念也作「入出息念」,或略為「安般念」,就是「緣於呼吸的心念修學」。 《出曜經》、《五事毘婆沙論》將安般念與不淨觀,並譽為佛法修學的「二甘露門」(大正大藏經四冊第六九八頁、二八冊第九八九頁),不過,就適用的廣度、方 便性與副作用來看,安般念有可能是略勝一籌的,因為呼吸一直伴隨著我們,只要還有一口氣在,隨時隨地都可以成為自己觀照的對象(所緣)。
五、佛陀教導安般念,是從一早入城乞食的「守護六根」說起的,可見得安般念的修學,不是坐下來觀呼吸才開始,事先的心念收攝等準備功課,是其重要基礎。
skip to main |
skip to sideba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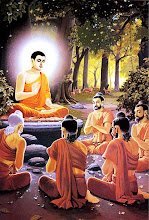




揭开附佛外道的真面目,以免让人误入岐图,愿正法常住
About M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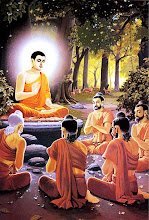
- --==《正法常住》==--
- 礼敬于世尊、应供、正等正觉者。 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 再皈依佛、再皈依法、再皈依僧. 三皈依佛、三皈依法、三皈依僧. 愿正法常住
Visitors
南無本师释迦牟尼佛



Blog Archive
-
▼
2009
(108)
-
▼
May
(56)
- 085.勇者富樓那
- 084.二十億耳的精進
- 083.質多羅居士的不必相信佛陀所說
- 082.不要只是相信
- 081.舍利弗的「深信」
- 080.無不散的筵席
- 079.舍利弗對昔日老友的關懷
- 第三篇 僧伽 078.舍利弗的得解脫
- 077.在家居士的安樂八法
- 076.念佛等六念法門的開示
- 075.戰爭與勝負
- 074.興邦衛國的七不衰法
- 073.說與不說之間
- 072.意業為最重 ──優婆離外道居士的歸依
- 071.淳陀所喜歡的清淨修行法門──浮起來啊!石頭
- 070.[和+心]破錯誤的惡業報應論
- 069.複雜的業報
- 068.愚蠢的善宿
- 067.企圖找尋世界邊緣的赤馬仙
- 066.自以為是創造主的大梵天王
- 065.遍尋不著瞿低迦的識
- 064.只能依附身心生存的識
- 063.同一個識在輪迴嗎? ──嗏帝比丘的邪見
- 062.誰受苦樂
- 061.焰摩迦的我見
- 060.午睡是癡的表現嗎?──薩遮迦的論辯挑戰(之二)
- 059.有真我嗎?──薩遮迦的論辯挑戰(之一)
- 058.眾多邪見的原因
- 057.佛陀的沈默回應
- 056.不能導向涅槃的無記 ── 一個治療箭傷的譬喻
- 055.佛陀的無記回答
- 054.藝人塔羅布吒的悲泣
- 053.誰來享用祭品?
- 052.擔心來生嗎?
- 051.勇猛銳利的隨死念
- 050.死亡的壓迫
- 049.一舉突破的觀空法 ──大空經的觀法
- 048.逐層突破的觀空法 ──小空經的觀法
- 047.就像郵遞馬車的次第接力
- 046.都說止觀二法
- 045.安般念的教說因緣
- 044.就像馴服一頭牛
- 043.就像六隻不同類的動物
- 042.在竹竿上特技表演的啟示
- 041.鷹與猴的死亡之路
- 040.時時刻刻不染著
- 039.佛法的修根
- 038.鹿住優婆夷的疑惑
- 037.同理心──自通之法
- 036.優填那王的讚歎 ──性慾的降服方法
- 035.法尚應捨,何況非法的感官欲樂 ──阿梨吒比丘的邪見
- 034.以欲愛斷欲愛
- 033.大師就說調伏欲貪
- 032.在黑牛與白牛之間
- 031.身苦心不苦
- 佛陀的一生
-
▼
May
(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