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再研究
今天的开示是有关第三圣谛──苦灭圣谛,即涅盘──的六堂开示的第五堂。今天我们要从瓦查各达
外道的开展来讨论它。
从诸经里,我们知道瓦查各达问佛陀与其它阿罗汉许许多多的问题,时常是同样的问题。从中可知他
很迷惑,但并非迷惑至令他放弃:他是一个真正的寻法者。
有一次,他去见目犍连尊者,问道:
1. 「目犍连大师,世界是永恒的吗?」
目犍连尊者说了什么?他是否说:「我想……」或「依我的看法……」或更糟的是「我觉得……」?
没有,目犍连尊者是阿罗汉,是佛陀的上首弟子,因此他的回答是:
「瓦查,世尊没有宣说:『世界是是恒的。』」
这是真正释迦子的回答。
瓦查各达接着问:
2. 那么,目犍连大师,世界是不永恒的吗?
3. 世界是有量的吗?
4. 世界是无量的吗?
5. 名与色是一体?
6. 名是一物,色则是另一物?
7. 如来死后是否存在?
8. 如来死后是否不存在?
9. 如来死后是否既存在又不存在?
10. 如来死后是否既非存在亦非不存在?
对于这一切问题,其回答是:
「瓦查,世尊没有宣说:『世界是是恒的。』」
瓦查各达问的问题是见,根据忆测、猜测与理论:形而上学。当我们不正确地知见诸法,我们根据自
己的无知见解、甚至是梦想来忆测。于是我们可能会下定论,说阿罗汉般涅盘后依然存在,若是如此
,无量世界将会无时无刻不会没有无量的佛陀与其它阿罗汉,这听起来很美妙,不是吗?反之,我们
可能会了解,说阿罗汉般涅盘后依然存在便是说四圣谛是无稽之谈,所以我们回避它,说阿罗汉既存
在又不存在,或既非存在亦非不存在。这是形而上学可爱的一面: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制造任何解决
方法,如果它像是无稽之谈,我们还是可以制造玄学,以它来说服轻信者,说该无稽之谈是超越一切
的深奥真谛。
形而上学盛行于佛陀时代的印度的外道圈子里,在那之前也盛行,如今也盛行,在每一个地方都盛行
:跟无明一样,形而上学自然地产生。它便是组成宗教的东西,包括现代世界的主要宗教:所谓的现
代科学。现代科学自认最令人赞叹的便是科学是以试验与理智为根据:它不根据理论,而是根据从试
验中获得的事实。这好像很令人钦佩,但却没有提到所收集的资料及所作的分析都是根据个人的形而
上学、根据他认为自己将会找到的、根据自己想要找的:「中立的观察员」这一词是自相矛盾的。现
代科学的形而上学是认为只有物质是真实的(包括心),这意味量等于质。许多透过眼、耳、鼻、舌
、身与意体验的快乐经验是好的,越多越好。越来越多便是越来越好。如果它们不是快乐的经验,那
便把它们改造成快乐的。创造越来越多,出产越来越多,卖越来越多,买越来越多,消费越来越多,
便会越来越快乐。这是现代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这是为何它们是商业的侍女。
形而上学已经渗透了现代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直到在每一个领域滋长,包括形而上学本身。问题(课
题)越来越多,答案(论文)也越来越多:这过程称为「研究」。正如我们所见,永无止境的研究并
不能带来对真实法越来越深奥的了解,反之导致对什么是重要的及什么是不重要的越来越迷惑。由于
对现代科学的迷惑理念盲信,我们可能会认为佛法有缺陷:「佛陀并没有回答一切问题!时代已经改
变!在佛陀时代的印度,他们并不知道今天我们所知道的事!」
瓦查各达也以为佛陀的教法有缺陷,这也是因为佛法没有提到形而上学的理念。因此,他问目犍连尊
者为什么其它沙门会回答他的问题,但佛陀却不会。目犍连尊者解释:
「瓦查,外道的沙门如此视眼……耳……鼻……舌……身……意:
『这是我的』,
『这是我』,
『这是我的自我』。」
透过正法,每次我们都回到同一件事。需要被发现的已经完全被佛陀发现了:不需要再研究。现代科
学的微弱知识不能够为佛陀的教法带来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已经被佛陀重新发现与解释的研究过程(
导向苦灭之道)并不需要改进,也不能被改进。因此,在佛陀时代,许多人了知现代科学的众弟子不
了知或不能够了知的事:在佛陀时代的印度,许多人知见涅盘──苦的息灭。
根据佛陀所教的步骤,首先他们修习止禅,也就是开展所需的工艺,以便能够收集必要的根本数据:
知见究竟名色诸行法每秒钟以上万亿次数的速度生、住、灭。接着,他们修习观禅,研究所收集的根
本资料。研究结束时,所获得的唯一真正存在的结论是诸行法灭尽:涅盘。缘于证悟了涅盘,一切问
题都结束──业行结束;证入般涅盘时,诸行完全结束。如果要说的话,他们唯一的形而上学是对佛
陀的证悟的信心:当他们自己也证悟时,信转变成智。
目犍连尊者向瓦查各达解释这种真正佛教的研究的结果:
「然而,瓦查,阿罗汉、正等正觉者如此视眼……耳……鼻……舌……身……意:
『这不是我的』,
『这不是我』,
『这不是我的自我』(。
因此如来被问及这些问题时,他不给与答案。」
接着,瓦查各达告诉目犍连尊者他刚见过佛陀,问佛陀同样的问题,以及获得同样的答案:
「真是奇妙,目犍连大师!真是令人惊叹,目犍连大师!关于主要的事,导师与弟子的义理与词句多
么的互相符合、一致,不相违背。」
或许这并不太令人惊叹,因为真正佛教研究的结论是了知真谛,而真谛是永远一样的。因此,无论是
目犍连阿罗汉或乔达摩阿罗汉,其结论在要义上必定只有同一个。然而,现代科学的种种结论是永远
不一样的。在同一个时候,便有许多不同的结论,甚至互相冲突的结论,而且它们一直根据「最新的
研究」在改变。这是对于真谛的形而上学式「铁一般的事实」的本质:迷惑。
同样地,形而上学式的探讨佛法方式导向非法。我们无法根据正确的步骤,例如无法知见过去诸世的
究竟名色法。我们可能因此坚持,唯有在有灵魂存在之下(对世俗谛与真谛迷惑),从一生轮回到另
一生才可能发生。接着,因为我们知道佛陀说没有灵魂,我们下定论地说,因为听众愚痴,佛陀才说
从一生轮回到另一生,事实上输回只是剎那至剎那间的事:换言之,我们断言说佛陀说谎。接着,基
于真正形而上学学者的我慢,我们争论且我封为权威,误导自己与他人。同样地,当我们的研究贫乏
,我们可能会断言佛陀教导的无我是指在究竟上一切法都是空的:也就是说,事实上它们完全不存在
。接着,基于真正形而上学学者的我慢,我们对「空」创造一个既庞大且复杂的形而上学法网,对于
轻信者,它显得无限地深奥。佛陀解释,一共有六十二种如此对世界创造出来的形而上学,每一种都
是邪见。
这种形而上学的迷惑衍生自贫乏、导向对四圣谛无明的研究。有一次,佛陀向瓦查各达解释:
「瓦查,由于不知、不见、不透视、不随觉、不通达、不分辨、不分别、不检查、不详细检查、不直
接识知:
1. 色、受、想、行与识(第一圣谛);
2. 其集起;
3. 其灭尽;
4. 导向它灭尽之道
这种种见至在世间生起。」
然而,当我们知见、透视、随觉、通达、分辨、分别、检查、详细检查及直接识知色、受、想、行与
识,我们知见它们的确存在,只是非常短暂,即是说它们是无常的。它们的无常意味它们是苦,它们
的无常与苦则意味它们是无我:世界并不是空的,而是无我:我的观念是形而上学,是不切题的。
有一次,瓦查各达不问其它形而上学的问题,而只问一个,当时佛陀便很清楚地表示这〔是形而上学
的问题〕:
「现在,乔达摩大师,是否有我?」
佛陀保持沉默。瓦查各达接着问:
「那么,乔达摩大师,是否没有我?」
佛陀再次保持沉默。随后瓦查各达便起身离去。
天人师的这种行为是不是很奇怪?不。因为阿难尊者问佛陀为什么不回答时,佛陀解释:
「阿难,瓦查各达外道问我『是否有我』时,如果我回答『有我』,那便是认同那些常见论者的沙门
与婆罗门。
他问我『是否没有我』时,如果我回答『没有我』,那便是认同那些断论者的沙门与婆罗门。」
在此,我们可能会掉入魔王的陷阱,心想:「啊!那就是说既有我又没有我!」但这完全不是佛陀的
意思。他只是说,无论我们怎么看我,那都是错误的想法:对我的假设是错的。佛陀知道,允许对我
的假设会带来迷惑。
「阿难,瓦查各达外道问我『是否有我』时,如果我回答『有我』,这对我来说是否符合所生起的『
诸法无我』的智慧?」
「不,尊者。」
当他问我『是否没有我』时,如果我回答『没有我』,原本已经迷惑的瓦查各达外道将会陷入更大的
迷惑,心想:『看来以前我所拥有的我现在已经不复存在了。』」
唉!可怜的瓦查各达的形而上学带给他极大的迷惑。但他继续努力,一而再地去见佛陀,与佛陀讨论
。且让我们再听一听。这一次,瓦查各达问佛陀,佛陀执持十种形而上学的见解的哪一种:世界是永
恒的,还是不永恒的;如来死后存在还是不存在;等等。每一次,佛陀都说他不执持该见。接着,瓦
查各达问: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乔达摩大师?
每当问及这十个问题的每一项,乔达摩大师都回答:『我不执持该见。』
乔达摩是见到什么怖畏,致使他不执持这些见的任何一个?」
对于每一项,佛陀都给与同样的解释。举例而言:
「瓦查,『如来死后存在』此见是见林、见的荒野、见的扭曲、见的犹豫、见结。它有苦、有困惑、
有恼及有热恼(;它不导向厌离、不导向离欲、不导向灭尽、不导向寂止、不导向证智、不导向菩提
、不导向涅盘。」
接着,佛陀给与结论:
「见此怖畏,我不执持这些见的任何一个。」
接着,瓦查各达问:
「乔达摩大师是否执持任何形而上学?」
佛陀解释:
「瓦查,形而上学是如来已经舍弃的。瓦查,如来已知见:
色如是……
受如是……
想如是……
行如是……
识如是……。」
在此,佛陀解释,阿罗汉已经收集了根本资料,也就是说他已经知见过去、未来、现在、内、外、粗
、细、劣、胜、远及近的究竟名色法。
接着他的分析。佛陀解释:
〔对于这十一种五蕴的任何一者,阿罗汉已知见(例如):〕
「识的集起如是,
识的消逝如是。」
这就是说,他知见十一种究竟名色法生灭。他知见第一圣谛(苦)及第二圣谛(苦集:苦的因)。这
些圣谛不是形而上学,是真实法。
佛陀解释,由于这对于真实法的智慧,阿罗汉舍弃了形而上学,证悟了至上法:
「因此,我说,透过毁灭、离欲、灭尽、舍离、遣离一切像想、一切假设、一切我作、我的造作及潜
伏性的我慢,如来已经透过不执取而解脱。」
正如目犍连尊者与佛陀之前所解释,只要这一切法存在,就有执取形而上学的潜伏能力,因为它们是
形而上学的缘:透过阿罗汉道,这些缘不复存在。
唉!对于瓦查各达,它们还存在,这是为何他坚持形而上学,问道:
「乔达摩大师,当比丘的心如此解脱,他会投生到哪里?」
「瓦查,『投生』这一词并不适用。」
「乔达摩大师,那么是他不投生?」
「瓦查,『不投生』这一词并不适用。」
「乔达摩大师,那么他是既投生又不投生?」
「瓦查,『既投生又不投生』这一词并不适用。」
「乔达摩大师,那么他是既非投生又非不投生?」
「瓦查,『既非投生又非不投生』这一词并不适用。」
在此,佛陀再次言明瓦查各达的假设是错的。当形而上学学者的假错被否定时,会发生什么事情?疑
生起:
「我在此陷入了困惑,乔达摩大师,我在此陷入了迷惑,之前透过与乔达摩大师交谈而获得信心现在
都消失了。」
可怜的瓦查各达!发生在他身上的事在一切时候都在发生,尤其是现在。我们探讨佛法,以为在其中
能够寻获什么来支持我们的不切题形而上学。由于佛法没有给予这类答案,我们对佛陀的证悟失去了
信心。这是我们「改进」或「现代化」佛法的因缘。且让我们看一看佛陀进一步向瓦查各达解释这种
现代现象:
「瓦查,这足于令你困惑,足于令你迷惑。
瓦查,因为此法深奥、难见)、难懂、寂静、殊胜、只依靠推理不能证悟、微细、当由智者体证。
在你执持其它见解、接受其它教法、认同其它教法、追求不同的修行、跟随不同的导师时,你很难了
解它。」
一时,瓦查各达对佛陀充满信心,走在正道之上,在下一刻,他却充满了疑,步入了邪道。当我们心
中执持其它见解地来探讨佛法时,所发生的便是这回事。同时看向两种方法,我们会得斗鸡眼,乖离
了八分圣道,步入了非法之道。
但瓦查各达很幸运,因为有佛陀引导他。这时候,佛陀说:
「因此,瓦查,我要反过来问你这个问题。你可根据自己认为适当的来回答。
瓦查,你认为怎样?假设有火在你面前燃烧,你是否会知道『此火在我面前燃烧』?」
「我会,乔达摩大师。」
假设我们点燃一支蜡烛,我们是否会知道「此蜡烛在我面前燃烧」?
「瓦查,如果有人问你:『在你面前燃烧的火依靠什么而燃烧?』被如此问及时,你会怎么回答?」
「被如此问及时,乔达摩大师,我会答:『此火依靠草与木柴而燃烧。』」
蜡烛依靠什么而燃烧?蜡烛依靠蜡与烛芯而燃烧。
「如果你面前,你是否会知道『在我面前的火已经熄灭』?」
「我会,乔达摩大师。」
如果该蜡烛燃尽了,我们否会知道「这蜡烛已经燃尽」?
「瓦查,如果有人问你:『在你面前熄灭的火朝哪一个方向离去:东、西、北或南?』被如此问及时
,你会怎么回答?」
「乔达摩大师,这是不适用的。该火依靠草及火柴为燃料来燃烧。当柴草烧完时,如果不增添燃料,
在没有燃料之下,火便算是熄灭了。」
如果检视蜡烛,我们便会看到蜡与烛芯。如果我们点燃烛芯,它便会点烧,烧到热蜡时,稳定且明亮
的火便出现。如果有人问我们:「在它出现在烛芯之前,是否有稳定且明亮的烛火?它在哪里等着出
现?它从哪里来?」我们的回答是:「朋友,这是不适用的。当我点燃烛芯,直到它烧到热蜡时,稳
定且明亮的火便会出现。如果我不点燃烛芯,如果没有蜡,稳定且明亮的火便不会出现。」蜡烛燃尽
时,如果有人问我们:「火去了哪里?」我们的回答是:「朋友,这是不适用的。火已经熄灭,因为
使它存在的缘已经不复存在。蜡烛已经燃尽,已经没有蜡了。」我们的回答和瓦查各达的回答相同:
「这是不适用的。」对于有关阿罗汉投生的问题,佛陀的回答也是同样:阿罗汉已经关掉了所需要的
能源(所需要的贪爱能源),也就是说对这问题的假设是错误的。这就像是问香蕉是用电油或柴油来
操作。
佛陀进一步解释:
「同样地,瓦查,如来已经舍弃了人们依它来形容如来的色。他已经根除它,使它变成好像棕榈树桩
,已经断除它,使它不再能够在未来生起。瓦查,在色方面,如来已经解脱,他深奥、无量、犹如海
洋无法测量。『投生』这一词并不适用;『不投生』这一词并不适用;『既投生又不投生』这一词并
不适用;;『既非投生又非不投生』这一词并不适用。」
对于受、想、行与识,佛陀也给与同样的解释。
在此,佛陀解释,阿罗汉深奥、无量、犹如海洋无法测量。我们可能会忘记这只是一个譬喻,反之认
为它是神秘的形而上学:「啊哈!你看!至上的成就便是与深奥、无量、无法测量的真如合为一体!
遍满一切宇宙的心!原来的心!空!」接着,我们可能会依此虚假的知识创造庞大的形而上学:这是
我们最不幸的恶业,衍生自形而上学的坏气氛,即想象、假设、我作、我的造作、潜伏性的我慢:简
而言之,那便是因为贪、瞋、痴。执持这种见,我们从深奥、无量、无法测量的迷惑,去到更深奥、
更无量、更无法测量的迷惑:继续生死轮回,甚至投生为动物或投生到地狱里。
瓦查各达并非如此。他恭敬地聆听佛陀的教导,由于他并不愚蠢,他了解佛陀的教法如何超越一切形
而上学。为了解释这一点,他也举出一个非常好的譬喻:
「乔达摩大师,假设离村庄或城镇不远处有棵娑罗树,无常去掉了它的枝叶,去掉它的外皮与软木,
以致后来在除掉枝叶、外皮与软木之后,它变得纯净,整个都是心木。
同样地,乔达摩大师的开示已除掉枝叶、外皮与软木之后,它纯净,整个都是心木。」
以此宣示重新获得、具备智慧的信心,瓦查各达再次(热忱地)归依佛、法、僧。
佛陀的教法已经去掉了想象与假设这些枝叶,去掉了我作、我的造作、潜伏性的我慢这些外皮与软木
:佛陀的教法是正法,它纯净,整个都是心木。
瓦查各达再次请教佛陀,但这时候他不再问形而上学的问题 。这一次,他的问题既简要又直接:
「希望乔达摩大师能够简要地教我有关善与不善。」
这是很严肃的切身问题。因为如果不知道善与不善之间的差别,我们怎么会开始想要证悟涅盘?因此
,佛陀直接地回答他的问题,解释贪瞋痴是不善,与它们相反的则是善;解释杀生、偷盗、邪淫、妄
语、两舌、恶口、绮语、贪婪、瞋恨与邪见是不善,戒禁这十恶行则是善。佛陀也解释,贪爱灭尽时
,比丘不再投生、梵行已立、应作皆办等等。
以为阿罗汉道果是属于佛陀专有的范畴,瓦查各达问是否有任何比丘也达到这种境界。佛陀解释,达
到这种境界的比丘不只一百位,不只两百、三百、四百或五百位,而是远比这数目更多的比丘。接着
,对于比丘尼,瓦查各达问同样的问题,也获得同样的答案。接着,瓦查各达问是否有任何在家男信
徒证悟成为阿那含圣者,死后肯定会投生到梵天界,在该处证悟阿罗汉道果。佛陀给与同样的答案。
关于证悟成为阿那含圣者的在家女信徒、证悟成为斯陀含圣者的在家男信徒、证悟成为斯陀含圣者的
在家女信徒、证悟成为须陀洹圣者的在家男信徒、证悟成为须陀洹圣者的在家女信徒,佛陀都给与同
样的答案:每一次都说不只一百、两百、三百、四百或五百,而是远比这数目更多。这一切弟子(出
家众与在家众)都肯定会灭尽生死轮回与痛苦。
对于这点,瓦查各达举出一个有关佛陀所教的梵行多么圆满的详尽分析,然后给与结论:
「乔达摩大师,由于诸比丘、诸比丘尼、白衣在家男信徒(包括过着梵行生活者与享受欲乐者)及白
衣在家女信徒(包括过着梵行生活者与享受欲乐者)成就于此法,此梵行如是圆满。」
在此,瓦查各达再次举出一个很好的譬喻来解释:
「就像恒河倾向大海、斜向大海、流向大海及融入大海,同样地,乔达摩大师的出家众与在家众倾向
涅盘、斜向涅盘、流向涅盘及融入涅盘。」
瓦查各达一而再地、热忱地归依佛、法、僧。但这一次他的归依圆满到他请求出家。成为瓦查各达尊
者之后,他实行比丘的修行(增上戒、增上心与增上慧),在两个星期之内,便成为阿那含圣者。接
着,他向佛陀请教更进一步的指导,以便达到梵行的目的:阿罗汉道果。佛陀教导向如何更进一步地
修习止观禅法。他照着修行,不久之后,在独处、远离社群、精进、热诚与决意之下,瓦查各达尊者
证悟了三明:宿住随念智、天眼智与漏尽智。瓦查各达尊者已办了应作的,已遵从佛陀的指导,成为
了阿罗汉。
拥有了阿罗汉的三明,瓦查各达尊者不需要再作任何研究。他已经得到佛陀与其它一切阿罗汉所得到
的结论。透过证悟涅盘,无明、爱与轮回的燃料已经烧完了。瓦查各达尊者喜悦地诵出此偈:
「三明为我有,我善于止禅。
我已得自利,完成佛所教。」
后来,见到一些比丘去见佛陀,他请他们以他的名誉、以首顶礼佛足,再说:「尊者,瓦查各达比丘
以他的头顶礼世尊之足。」
接着他说:「世尊已受我顶礼,善逝已受我顶礼。」
诸阿罗汉已经断除了潜伏性的我慢,因此他们自然地很谦虚。基于同样的原因,他们不会四处去向大
众说自己的禅修与成就:这种事不单只是我慢、不谦虚的相,而且是佛陀在戒律上不允许的。因此,
阿罗汉向佛陀说自己的阿罗汉道果成就时,他们会以间接的方式来说,例如瓦查各达尊者的方式。但
那些传达讯息的比丘们并不知道该讯息的含意。因此佛陀解释:
「诸比丘,以自己的心涵盖他的心之后,我已经知道瓦查各达比丘:『瓦查各达比丘已证悟三明,拥
有大神力、大威力。』
而且诸天神也这么告诉我:『瓦查各达比丘已证悟三明,拥有大神力、大威力。』」
谢谢。
绝对的分别
今天的开示是有关第四圣谛──导向苦灭之道圣谛,即导向涅盘的八分圣道的第一堂开示。今天我们
要整体地讨论八分圣道,以及简要地讨论个别的道分。
第一次说法时,佛陀便已解释两种毫无目标之道,以及一种有目标之道,即八分圣道:
「诸比丘,有两种极端是出家人所不应当从事的。是那两种呢?一种是沉迷于欲乐,这是低下的、粗
俗的、凡夫的、非圣的、没有利益的行为。」
这种极端之道是六根之道,或可说是六分愚蠢道:可喜之色、声、香、味、触及受、想等等之道。
「另一种是自我折磨的苦行,这是痛苦的、非圣的、没有利益的行为。」
这种极端可说是六分超极愚蠢道:不可喜之色、声、香、味、触及受、想等等之道。这两种愚蠢之道
导向盲目、无明、烦恼、痛苦与继续生死轮回(甚至投生到地狱)。
「如来发现的中道避免这两种极端。此中道引生彻见、引生智,导向寂、亲证智、正觉、涅盘。此中
道是什么?那就是八分圣道,即正见、正思惟、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
八分圣道组成三蕴(三组)。法施比丘尼:佛陀称赞她为解释佛法第一的比丘尼)曾经向她的前夫毘
舍佉解释每一蕴:
1. 正语、正业及正命这三项组成戒蕴。
2. 正精进、正念及正定这三项组成定蕴。
3. 正见及正思惟这两项组成慧蕴。
修行八分圣道时,便是在修行戒、定与慧,但却不能说修行戒、定与慧便是修行八分圣道。法施比丘
尼解释:
「贤友毘舍佉,这三蕴曾不包括在八分圣道之内,但八分圣道则包括在这三蕴之内。」
这是什么意思?它的意思是,如果我们布施、持守五戒、很罕有地花了二十分钟马马虎虎地专注于呼
吸、偶而在驾车去工作及去店或回来时听录音带的佛法开示,虽然这些作为在很小的程度上也算是修
行戒、定、慧,但它们并不算是修行八分圣道。即使我们去禅修三个月、持守八戒、培育禅那,这也
不算是修行八分圣道。八分圣道最低的程次是须陀洹道:它把我们带到涅盘,便像河流之水会把我们
带到大海里。佛陀解释:
「诸比丘,正如恒河斜向大海、倒向大海及倾向大海,同样地,培育与修习八分圣道的比丘也斜向涅
盘、倒向涅盘及倾向涅盘。」
唯有当我们进入了朝向涅盘之流,八分的每一分才成为道分。唯有圣者已经进入了圣道:这是用不着
说的。佛陀解释:
「此八分圣道是流,拥有此八分圣道者是入流者(须陀洹)。」
因此,虽然八分圣道最低的层次是须陀洹道,但却可以更高,因为它可以是更高层次的圣道:斯陀含
道及阿那含道。然而,证悟阿罗汉道时,该道不再是八分圣道,而是十分圣道。
然而,只要我们还是无明凡夫,我们的道就不是八分圣道。但是我们可能有时候会修习这些分。在这
种情况之下,每一分都是佛陀所说的世间分:
有漏、
福分、
带来有执着的果报
这并不是道分。修习这些世间分的果报只是投生到善趣:虽然它们是非圣的果报,但还是乐报。只要
我们的正见是属于世间的,它便是不肯定的:我们还可能执取邪见,实行非圣寻,甚至步入导向投生
恶趣的八分邪道。这是为何佛陀不曾说「八分世间圣道」:这一词是自相矛盾的。
然而,一旦成了圣者(一旦证悟了涅盘),这八分便会一同生起,组成八分圣道。在这种情况之下,
每一分都是佛陀所说的出世间分:
圣
无漏
出世间
道分。
修习八分圣道的果报是肯定最迟再过七世便会达到阿罗汉果(生死轮回与痛苦的尽头)。成为圣者时
,我们已经根除了身见,对业报法则拥有绝对的信心,已经破除了对佛陀的证悟及导向解脱的正道的怀
疑。那时候我们的正见便会使得我们不能够再执取邪见,不能够再实行非圣寻,不能够再步入导向投
生恶趣的八分邪道。正见分别:绝对的正见绝对地分别。
在实修上,入流的含义是什么?入流便是很清晰地知见涅盘,就像清楚地看见山中清澈的湖里的鱼、
贝壳、鹅卵石等等一样。知见涅盘时,便会有佛陀所说的圣正定:其目标是涅盘。
佛陀解释,若要培育这种定,便需要培育五法:
「诸比丘,举进入且安住于初禅的比丘来说。诸比丘,这是五支圣定的第一种修习。」
第二种修习是第二禅,第三种是第三禅,第四种则是第四禅:这四个是四支。佛陀也把它称为正定。
然而,若要使正定成为道支,禅那的目标就必须是涅盘。若要使得我们的正定成为具备五支的圣正定
,我们必须修习回观过去的能力,以便了知我们已经知见涅盘:这是第五支,佛陀称之为省察相 。唯
有能够省察涅盘之相时,我们才能够知见我们是否已经证悟须陀洹道果、斯陀含道果等等,以及进一
步培育圣道。
圣正定是以涅盘为目标的禅那定:每当我们知见涅盘时,我们便是在禅那之中。但是圣正定并不能够
独自生起。它必须与八分圣道中的其余七分同时生起,即正见、正思惟、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
与正念。佛陀解释:
「具备这七分的心一境称为有依止、有资具的圣正定。」
换句话说,这八分互相配合运作:它们的前导者是正见。且让我们看一看它们怎样互相配合运作。
见是前导者。我们的见是我们看事物的方式:如果我们的见是唯物论,我们见一切事物为色法;如果
是唯心论,我们见一切事物为心;如果是民主论,我们见一切事物为平等;如果是相对论,我们主观
地看待一切事物;如果是务实论,我们见一切事物为不依任何见(神奇的字眼是「实际」 );如果是
断见,我们见一切事物为无物。无论是什么见,它为领导我们的身、语、意作为:它是我们的生命道
路的前导者。举例而言,以受到高度尊敬的务实论为前导者,在国会及家庭里的现代政治是毫无原则
且迷惑的。
然而,当我们的前导者是正见时,迷惑便不会产生。佛陀解释:
「正见如何作为前导者?
他了知邪见为邪见、正见为正见:
这是他的正见。」
拥有正见时,我们对事实有足够的了解,以便能够绝对地分别正见与邪见。当然,如果没有正见的话
,这是不可能的。
佛陀解释:
「诸比丘,什么是邪见?
没有所施之物、没有所供养之物。(没有布施的作为。)
没有善业或恶业的果报。(不需要分别善恶,因为无业无果报。)
没有这世界,也没有其它世界。(没有轮回到其它世界。)
无父无母。(父母并不特别:他们不值得获得特别的待遇。)
没有化生的有情。(没有天神及其它诸如此类的有情。)
在这世间没有已经亲自透过胜智了知且宣布此世与他世的善德沙门与婆罗门。(诸阿罗汉与诸佛并不
特别,只是想象出来的人物。)」
这些古代邪见对我们来说是很熟悉的,因为它们构成了正统的现代见解。例如其教条是:
「基本上一切见解都是好的。」
「造恶是绝对自然的,你做什么都没有关系。」
「怎么说并不重要,重要的只是表达。」
「男女是绝对平等的。」
「绝大多数人是永远绝对正确的。」
「一切的涅盘都是同样的。」
「一切道路都能够导向涅盘。」
「僧团(第三宝 )其实便是走在任何一条导向任何一种涅盘的一切众生。」
「法(第二宝)其实便是一切宗教的教法。」
「基本上,我们全部都是佛陀(第一宝)。」
这样的见解绝对地分别了分别。由于受到贪欲、我慢及绝对的无明束缚,它们是绝对的邪见。
佛陀解释正见:
「诸比丘,什么是正见?
有所施之物、有所供养之物。(有布施的作为。)
有善业及恶业的果报。(需要分别善恶,因为有业及果报。)
有这世界,也有其它世界。(有轮回到其它世界。)
有父有母。(父母是特别的:他们值得获得特别的待遇。)
有化生的有情。(有天神及其它诸如此类的有情。)
在这世间有已经亲自透过胜智了知且宣布此世与他世的善德沙门与婆罗门。(诸阿罗汉与诸佛绝对特
别地睿智。)」
由于见是我们的价值观的前导者,它也是我们的思惟的前导者。拥有正见时,我们作出绝对的分别。
佛陀解释:
「正见如何作为前导者?
他了知邪思惟为邪思惟、正思惟为正思惟:
这是他的正见。」
邪思惟有三种:
「诸比丘,什么是邪思惟?
1. 欲贪思惟(贪欲、想要拥有、想要获得、想要继续。)
2. 瞋恨思惟(瞋恨与不喜。)
3. 伤害思惟(想要伤害别人。)」
「诸比丘,什么是正思惟?
1. 出离思惟(布施、想要施与、想要舍弃、知足、想要停止、稳固的梵行:最高的这种出离思
惟是舍离俗家而成为比丘或比丘尼。然而,比这更高的是舍离色、声、香、味等、以便成就禅修业处
的思惟。以此思惟,禅修者可以证悟禅那,甚至修习属于更高层次的出离的观禅。以此思惟,他可以
证悟至上的出离,即涅盘与阿罗汉道果:舍离生、老、死、愁、悲、苦、忧、恼,也就是舍离五取蕴
、舍离诸行。)
2. 无瞋思惟(对一切众生,包括人与非人,都心怀善意、慈爱。)
3. 无害思惟(关怀、悲愍一切众生,包括人与非人。)」
由于见是我们的思惟的前导者,它也是我们的语业的前导者。拥有正见时,我们作出绝对的分别。佛
陀解释:
「正见如何作为前导者?
他了知邪语为邪语、正语为正语:
这是他的正见。」
邪语有四种:
「诸比丘,什么是邪语?
1. 妄语(说不真实的话。)、
2. 两舌(说别人的坏话,说离间的话。)、
3. 恶口(说粗野、无礼、伤人的话。)、
4. 绮语(毫无分别地说无益的话:运动、轰动的新闻、家庭、无谓的统计等等。)。」
「诸比丘,什么是正语?
1. 戒禁妄语(只说真实的话,即使遭遇损失也在所不惜。)、
2. 戒禁两舌(避免说别人的坏话,但若在有需要时,则不心想离间地说。)、
3. 戒禁恶口(说有礼、适当且善意的话。)、
4. 戒禁绮语(有分别地说有益的话。我们可以和陌生人或很久没见的亲友互相问候,但不接下
去闲谈。我们可以说故事,但并不是为了娱乐,而是为了说明一个有益的课题。如果没有有益的话可
说,我们愿意保持沉默。)。」
由于见是我们的思惟的前导者,它也是我们的身业的前导者。拥有正见时,我们作出绝对的分别。佛
陀解释:
「正见如何作为前导者?
他了知邪业为邪业、正业为正业:
这是他的正见。」
邪业有三种:
「诸比丘,什么是邪业?
1. 杀生(残暴地剥夺了其它众生的生命:蚊子、蟑螂、蚂蚁、老鼠、鱼、牛、猪、胎儿、战场
上的男人、女人及小孩等等。)、
2. 偷盗(盗取别人的财物、逃税、用盗版计算机软件等等。)、
3. 邪淫(与别人的伴侣、未婚夫妻等有染、强奸等等。)。」
「诸比丘,什么是正业?
1. 戒禁杀生(心怀善意地与其它众生和平过活。如果在我们的家里或花园里有害虫,我们与牠
们和平地过活,或者采用不会杀死牠们的方法来解决。)、
2. 戒禁偷盗(我们不拿取不属于我们的东西,我们缴税,只用合法的计算机软件等等。)、
3. 戒禁邪淫(我们满足自己的丈夫或妻子。)。」
我们必须获取生活的四种必需品:衣、食、住、药。这是我们的活命。由于见是我们的思惟、语业与
身业的前导者,它也是我们的活命的前导者。拥有正见时,我们作出绝对的分别。佛陀解释:
「正见如何作为前导者?
他了知邪命为邪命、正命为正命:
这是他的正见。」
邪命有许多种。一般上,邪命是透过邪语及邪业来活命。佛陀解释,对于在家人来说,从事五种买卖
也是邪命:
「诸比丘,在家信徒不应从事五种买卖。是哪五种?买卖武器、人、肉、酒与毒药。」
这些买卖可以不透过邪语及邪业来进行,但其结果等同邪语与邪业。举例而言,武器(例如飞弹、炸
弹)与毒药(例如杀虫剂、杀草剂)的用途只有一个:伤害、杀害与毁灭。有了酒,也就有了邪语与
邪业。
对于比丘,佛陀解释:
「诸比丘,什么是邪命?
诡计(为了获得崇敬、喜爱而言行:提及自己〔殊胜〕的修行。)、
说话(为了讨取在家人的欢心,他毫不分别地说、先说、谈论自己、甚至说废话、爱抚小孩
等等。)、
暗示(暗示以获得供养。)、
贬抑(他呵责在家人、批评他们、讽刺他们、说他们的闲话等等。)、
以利套利(他给在家人食物、花等,以便受到喜爱。)。」
佛陀还解释了比丘不应该做的许多其它事情 ,例如比丘不可以算命、念咒、洒圣水及行医:这些是佛
陀绝对禁止的。
「诸比丘,什么是正命?在此,圣弟子舍弃邪命,以正命过活。」
一般上,正命是透过正语及正业来活命。对于在家人来说,那便是好又真诚的工作,不需要伤害任何
众生;对于比丘来说,它便是依戒律过活。
思惟是意业,语是语业,业是身业,命则是身业及语业。若要造作这些业,我们必须付出精进。如果
邪见是精进的前导者,它便是邪精进;如果正见是精进的前导者,它便是正精进,因为它的目标是正
确的,最终其目标是涅盘。佛陀解释:
「他致力于舍弃邪见而进入正见,这是他的正精进。
他致力于舍弃邪思惟而进入正思惟,这是他的正精进。
他致力于舍弃邪语而进入正语,这是他的正精进。
他致力于舍弃邪业而进入正业,这是他的正精进。
他致力于舍弃邪命而进入正命,这是他的正精进。」
正精进有四种:
「诸比丘,有这四勤。是哪四种?
1. 防护勤(我们透过持戒而不造邪语、邪业及邪命。举例而言,农夫原本想要用毒药来保护其
农作物,但却由于持戒而不实行。)、
2. 舍断勤(我们停止所造的恶。举例而言,用毒药的农夫停止再用毒药。)、
3. 修习勤(我们实行新的修行。举例而言,我们修习三种「福作事(pu¤¤akiriyavatthu)」
:我们布施、持五戒乃至八戒、修习止禅与观禅,以及修学佛法。我们甚至可能出家。我们的农夫也
可能研究出新的耕种方法,而不需要用毒药。
4. 随护勤(我们继续实行所做的善身语意业。举例而言,别的农夫可能会批评我们的农夫不用
毒药,但我们的农夫并不因此而再次采用毒药:他只是以微笑来响应另一位农夫的愚蠢。)
正如每一种业都需要精进,它也需要对所做的事有警觉心,记得怎么做:念。如果邪见是念的前导者
,该念便是邪念,因为其目标是错的;如果正见是念的前导者,该念便是正念,因为其目标是对的:
佛法,最终则是涅盘。佛陀解释:
「他正念地舍弃邪见而进入正见,这是他的正念。
他正念地舍弃邪思惟而进入正思惟,这是他的正念。
他正念地舍弃邪语而进入正语,这是他的正念。
他正念地舍弃邪业而进入正业,这是他的正念。
他正念地舍弃邪命而进入正命,这是他的正念。」
佛陀解释,正念有四种:
「诸比丘,什么是正念?在此,诸比丘,比丘以热诚、正知、正念安住于观身为身、观受为受、观心
为心、观法为法,去除对世间的贪欲及忧恼。」
佛陀也称这为四念处。建立了四念处,我们便能够依法对自己的身、语、意保持警觉:我们对身心本
质警觉,也警觉对它们做了什么。佛陀也把这解释为念根,念根显现为记忆良好:
「诸比丘,何谓念根?在此,诸比丘,圣弟子有念、拥有至上念与分别,能够忆起及随念很久以前所
做及所说之事。」
正念肯定会带来的成果是人们能够忆起很久以前所想、所说及所做的事:即使老了,记忆也不会衰退
。一般上,如果人们善于分别地、良好地、睿智地运用自己的心,他们便不会痴呆:会痴呆的人通常
是那些无戒无慧地过活的人。当然,基于唯物论,现代医学认为病因纯粹是物质。
明显地,依法地对身、语、意保持的念不可能是邪念,因为法是真实法。无论如何,佛陀也提到邪念
,但在此他是说记忆的能力。举例而言,邪念发生在足球员勤练踢球、抢球、骗对手等等:他的确对
自己的身体有警觉。其训练的一部分是对自己的心警觉。举例而言,他的教练与队长将会在开赛前给
他的球队说些激励的话,灌输他们自己多么的优越,以及该场比赛是多么的重要。接着,在足球场上
,每当冲劲退减时,他认为那是他对球队的优越失去了信心。因此他回忆教练所说的话,然后继续冲
刺:但是他的球队并不优越,该场比赛并不重要,因为整件事都是为了疯狂赚钱而组织的。因此,球
员的念处是不能反映真实的忆测及观念。无论如何,足球员在踢球时,他记得怎么踢球,而且依照方
法踢球,也能因此而成功,变得富有且出名,受到全世界千千万万人崇拜为偶像,受到媒体采访,受
邀到总统府受用晚餐。然而,该足球偶像的念的前导者是绝对疯狂的邪见,致使其念变成邪念。对于
歌星、明星、战争英雄、甚至熟练的屠夫、渔夫、奸商、假出家人等等,其情形也是如此。
现代心理学普遍化的其中一个最广泛的影响是人们分析自己的心,特别是别人的心:甚至有人以此谋
生。但这些分析只是以邪见为前导的忆测及观念。因此,现代心理学给与世间最大的遗产是以深奥知
识为名、越来越大的迷惑:这知识包括认为分别善恶是不好的。其结果当然是不能对佛、法、僧产生
信心。反之,唯有在把佛、法、僧窜改成「我」之下,才能够产生信心,而我们也就归依自己这个三
宝。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邪见?因为缺少智慧:不了知四圣谛。接着会发生什么事?佛陀解释:
「对于沉沦于无明中的愚人,邪见生起。
对于有邪见的人,邪思惟生起。
对于有邪思惟的人,邪语生起。
对于有邪语的人,邪业生起。
对于有邪业的人,邪命生起。
对于有邪命的人,邪精进生起。
对于有邪精进的人,邪念生起。
对于有邪念的人,邪定生起。」
这是缘起。缘于邪见,我们成为佛陀所说的「非善士」 。佛陀解释,比该非善士更加非善士的是认为
自己是善士的非善士:其邪道有十分,因为他甚至拥有邪智与邪解脱 。与其省察涅盘之相,他省察自
己所造的恶业,却认为那是善的。举例而言,将军检查军师的报告时、家庭主妇检查死在厨房里的蚂
蚁及蟑螂时、推销员回忆骗老妇女用存款买她不需要的东西时、狗回忆自己刚才作出的凶恶吠声时。
因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拥有佛法的智慧是很重要的。举例而言,如果我们我行我素,心想:「菩
萨没有导师,为什么我需要导师?我是自己的导师!」或者我们有导师,但却是对正法无明的导师。
缘于无明,我们可能相信涅盘是回到我们所说的原来本质、原本的心等等。我们可能会修禅,甚至勤
奋地修禅,以便证得我们认为很深乃至禅那的定力。我们可能沉入深睡,却误以为已经证悟涅盘。为
什么呢?因为我们认为涅盘只是一种心的境界(名法)。这么想时,我们甚至会认为必须透过六种感
官非常细腻、所谓不执着的耽乐来证悟涅盘:在大自然中散步、可爱的小孩、美丽的佛像等等,我们
不明白耽乐便是执着与贪欲。我们也可能认为必须透过所谓不执着的社工来证悟涅盘:探访病人、安
慰死人的家属、资助穷人等等,我们不明白社工便是对世间的贪欲及忧恼。由于对涅盘秉持邪见,我
们的整条道路是错的。我们甚至会相信佛陀指示要我们持戒与住在寂静处只是古印度的文化遗产:我
们可能认为可以窜改属于戒、定、慧的诸分,甚至认为它们便是八分圣道。缘于这些见,第一及第二
圣谛被人改成只是理论与观念;我们的无明已经被强化,变得不可渗透;我们离开涅盘甚远,一直越
离越远。
正见则不是如此。正见是因为「明」而生起:对于涅盘的明。佛陀解释:
「对于已达到明的智者,正见生起。
对于有正见的人,正思惟生起。
对于有正思惟的人,正语生起。
对于有正语的人,正业生起。
对于有正业的人,正命生起。
对于有正命的人,正精进生起。
对于有正精进的人,正念生起。
对于有正念的人,正定生起。」
生起的正定是圣正定,有学圣弟子便是透过它知见涅盘。但他还没有修习八分圣道到最高境界。
佛陀也解释阿罗汉:
「对于有正定的人,正智生起。
对于有正智的人,正解脱生起。
如是,诸比丘,有学者拥有八分,阿罗汉拥有十分。」
缘于八分圣道,我们成为圣者,是佛陀所说的善士。当然,比善士更加善士的是阿罗汉:他已做了应
做的,已成为无学者,已圆满地修习八分圣道,已以最好的方式效法其导师佛陀:他拥有绝对的智慧
、绝对的分别,已达到绝对至高的境界。
对于阿罗汉,佛陀说:
他智慧甚深、睿智、
善分辨道与非道、
已达到最高目标,
我称他为婆罗门。
谢谢。
skip to main |
skip to sideba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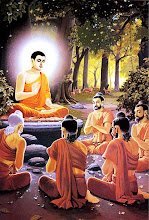




揭开附佛外道的真面目,以免让人误入岐图,愿正法常住
About M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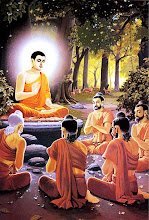
- --==《正法常住》==--
- 礼敬于世尊、应供、正等正觉者。 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 再皈依佛、再皈依法、再皈依僧. 三皈依佛、三皈依法、三皈依僧. 愿正法常住
Visitors
南無本师释迦牟尼佛



Blog Archive
-
▼
2008
(65)
-
▼
August
(27)
- 四圣谛──导向苦灭之道圣谛
- 四圣谛──苦灭圣谛 (第五堂)
- 四圣谛──苦灭圣谛 (第四堂)
- 四圣谛──苦灭圣谛 (第三堂)
- 四圣谛──苦灭圣谛 (第二堂)
- 四圣谛──苦集圣谛 (最后一堂)
- 四圣谛──苦集圣谛 (第三堂)
- 四圣谛──苦集圣谛 (第二堂)
- 四圣谛──苦集圣谛 (第一堂)
- 四圣谛──苦圣谛
- 四圣谛
- 三法印
- 013.佛陀普渡眾生了嗎?
- 012.佛滅後的「大師」
- 011.對佛陀最誠敬的供養
- 010.不聞雷聲的讚歎
- 009.久離恐怖的佛陀
- 008.佛陀如何面對謾罵
- 007.聖者的恬靜淡泊性格
- 006.如何知道聖者
- 005.能成就無量福道的教誡教化
- 004 .拒絕利用神通傳教的佛陀
- 003.佛陀的初轉法輪
- 002.佛陀的修學歷程
- 001 怎樣才是真正的讚歎佛陀?
- 活人自称佛菩萨转世,必为魔说!
- 佛陀的开示:佛菩萨为什么不以神通度众生?
-
▼
August
(27)
